
“现在,李怡楷,”她却掉转脸去对我妻子开腔了,怡楷在她威风凛凛的目光下镇静自若。“为了帮助你,我们必须要求你自觉自愿提出放弃公职。明天,我等着看你亲笔写的要求退职的大字报。下个月,你们二人还可领到工资,不过那是最后一次。所以,从今天起,你们就得省吃俭用,一分钱也不能浪费啦。别吃猪肉啦!”
我俩说不出话来了。我已经认罪,但他们还这样残酷无情。面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我们有什么办法?怡楷遵命写好大字报,贴了出去。一个还跟她讲话的女同事看了大吃一惊。“你神经错乱了,小李?你干什么要退职?你家里的情况还不够糟的吗?你不工作靠什么生活?你、小丁丁、还有肚子里的孩子,一家三口?”她声音里流露出真诚的关心。怡楷苦笑着回答:“十分感谢。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克服吧。”
教育工会召开了一次会员大会,宣布将我开除会籍。同时,我们被赶出新公寓,搬回筒字楼。过了几天,我俩又被校长叫去。“我们一直在重新考虑你们的问题。我跟人事处长说:‘老王,李怡楷已经有一个孩子,不久又要生第二个。你们不能这样对待她。让她保留工作,挣点钱养活一家三口。’她简直是宽仁厚德的化身。“现在你该明白什么是革命人道主义了。你自觉自愿提出放弃你的饭碗,而我现在把它还给你。革命人道主义,哪怕是一名极右分子的老婆也受惠。去吧,再贴一张大字报,感谢党的革命人道主义关怀。”
我俩又说不出话来了。这样令人咋舌的伪善完全超越我们朴素的道德观念。这种表面的反复无常其实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神经战,其目的在于打垮我们的精神,并强迫我们用自己的手为他们的不人道涂脂抹粉,为他们欺骗群众的阴谋效力。我感到十分沮丧,但当晚怡楷却平静地说:“他们掌握绝对权力,对咱们可以为所欲为。我们毫无办法,但是必须坚守对生活的信念。”
我的妹妹宁慧也在二十八中被打成右派,罪证就是《北京日报》重点报道过的她在区委召开的鸣放座谈会上的发言。她被免除副校长职务,降三级,到一个郊区农场监督劳动。他丈夫原是一名预备党员,受她株连被取消候补资格。在北大西语系任教的、我过去燕京的同事中,黄继忠多年来“追求进步”,是公认的大积极分子,鸣放期间十分活跃,后来被划为极右分子,被送劳动教养。吴兴华才华出众,既无“历史问题”,政治上又“要求进步”,已提升为副系主任,却因质疑在英语教学中要学习苏联也被戴上右派帽子。胡稼胎教授,尽管谨慎寡言,又深谙佛法,也因鸣放中有右派言论照戴帽子不误。赵萝蕤教授因爱人陈梦家教授被划为右派受刺激而患上精神分裂症。俞大絪教授也因爱人曾昭伦当上了大右派而心脏病发作。曾先生是当年的“进步教授”,中共的同路人”,贵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部副部长。这样一来,当年燕京一共五位英语教授,其中三位男的本人,两位女教授的男人,统统当上了右派。一家一个,无一幸免。在南开,我当年的紧邻、雷海宗教授也被打成右派。查良铮谢绝参加教师鸣放会,幸免于难,却因为抗日期间爱国参军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被判“管制三年”。
王佐良教授主编的《西方语文》季刊创刊号的撰稿人中有好几名右派,其中包括吴兴华和我。刊物的执行编辑、葆青的爱人道生,被划为极右。主编为“方向性错误”做了检讨,刊物改名为《外语教学与研究》。我为兴华翻译的《亨利四世》所写的评论,本来预定在第二期刊登的,无疾而终。右派的作品不得出版,但我被打成右派的消息还没传到《译文》,我译的《珍珠》才得以侥幸问世。
根据多年后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全国被打成右派的超过五十万人。当年一个汉朝的暴君用宫刑残害一位进谏的史官,从此成为千古罪人。相比之下,这场反右运动对知识分子群体施加残暴的精神阉割,更是千古奇闻。与此同时,在运动中涌现出的大批积极分子,在反右派的阶级斗争战场上立了汗马功劳,升官的升官,入党的入党。一代伪君子和告密者开始毒化民族的道德操守,为以后的政治迫害运动铺平了道路。
五
在等候我的处分正式批准期间,我继续在图书馆搞英文书刊编目。右派学生都装上卡车送去劳改了,只剩下我单独在一名北大英语专业毕业生严密监视下劳动。这个年轻人老滋老味,满口官方文件和《人民日报》社论的官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交给我编目的书刊中,有一批从俄文翻成英文的小册子,都是关押在斯大林的集中营里的受害者写的。他们在肉体和精神上遭受暴虐的悲惨经历像恶梦一样让我惊悸,而他们对自由的渴望不断在我心里回响。有一本小册子的名字是《去告诉西方吧!》。在静悄悄的、无人问津的图书馆里,我仿佛听见作者痛苦的呼号。但我纳闷,西方国家或者我的西方朋友们是否知道或者关心中国发生在我这样的人身上的事情。于副校长说得对:“不管干什么都要付代价的。”而在社会主义中国,为自由鸣放不仅要付出代价,而且要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
有一天,我年轻的监工把我叫到他办公桌面前,指着一堆美国出版的新书,都是我在运动开始前通过学校订购的,刚刚从日内瓦的中国大使馆寄到。“巫宁坤,这些书你还要吗?”他板着面孔问我。“你要的话就说要。你如不要,我就马上盖上图书馆的公章。”我一直在等着这些书,其中多半是我在芝加哥大学受教的老师们的最新学术著作;我怎么会不要呢?但是我怎么买得起呢,现在只剩下一个月的工资了?我一本一本拿起又放下,他可不耐烦了。“我还有革命工作要做,你也得回去劳动。不要浪费时间。”我捡起薄薄的一本,那是我的老师奥尔逊教授诠释英国诗人狄伦斯托玛斯诗作的专著,忍痛放弃了其它几本。当我手里抓着书离开他的办公桌往回走时,我听到他劈劈啪啪往我买不起的几本新书上盖上公章的声音,仿佛他们是该消灭的阶级敌人。那天夜晚,我很晚未睡,对照奥尔逊精湛的诠释重读托玛斯的一些感人的诗篇。在寂静的深夜,我仿佛可重新听到,在我回国的前一年,在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教堂,诗人热情澎湃的声音朗诵他自己的诗《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
当筋疲腱松时在拉肢刑架上挣扎,
虽然绑在刑车上,他们却一定不会屈服;
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
第二天下午,正准备结束在图书馆的劳动,我又被叫到我年轻的监工办公桌前面。“巫宁坤,我奉校领导指示通知你:关于你的处分决定已由国务院批准。”他用他最神气的官腔宣布。“17日下午二时整,上级派人到你宿舍来送你去接受劳动教养。你准时在门口守候,不得违误。为了给你充分时间做好必要准备,上级决定从明天起,免除你劳动两天。党对你如此宽大,你应感恩图报,努力通过强迫劳动改造思想,立功赎罪。回家以前,你到人事室去一下,在你的结论上签字。”
在人事室,那位雨果笔下的警官在等我。“过来在你右派问题的结论上签字。”他边说边递给我一张纸,上面打印着我的六大罪状,教我在那儿签字。我飞快地看下去,他却不耐烦了。“在这儿签字,别浪费我的时间。已经下班了。”我一言不发签了字。
(16)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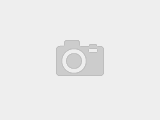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